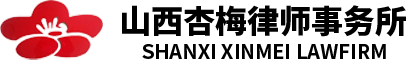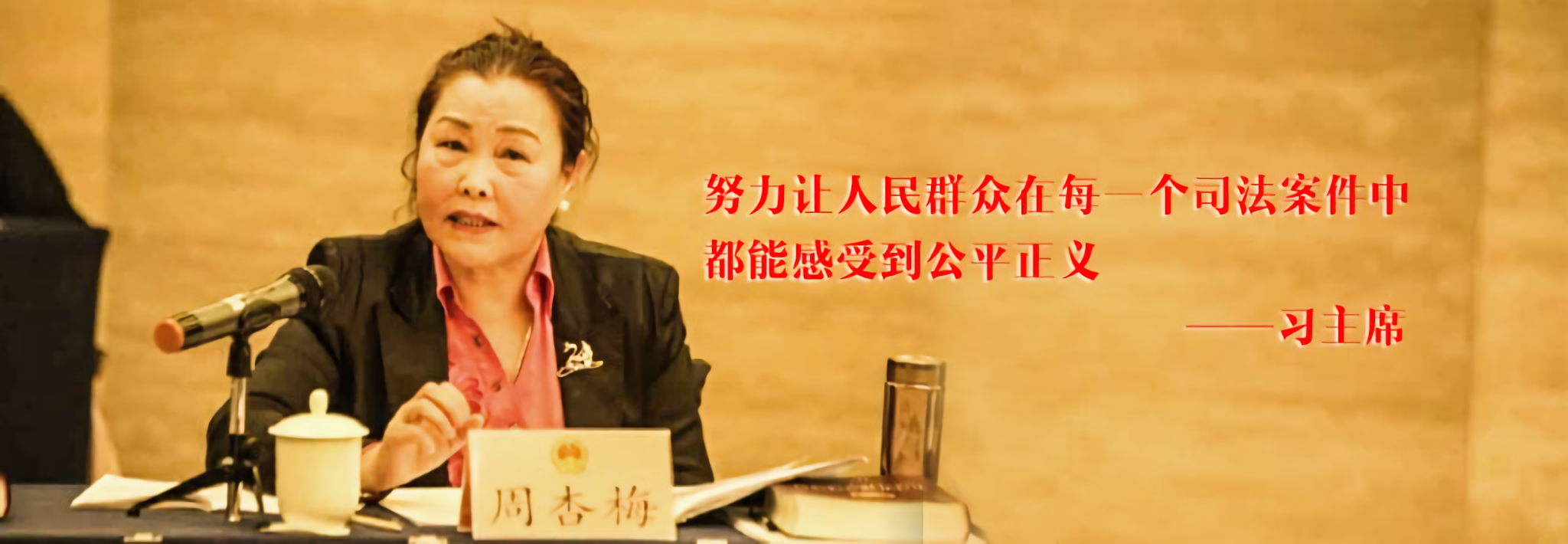在戏剧界有一句话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做任何行当都是这样的道理,包括做律师。做律师不懂法律无疑是不可能的,但仅仅懂法律,甚至把法律背得滚瓜烂熟,理解到它的骨头缝里,那也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律师,说不了还是一个最愚蠢、最倒霉的律师。律师是司法生活中的一种民间力量,由于它本身没有被国家意志赋于强制社会的权力,因此,它是在“说法律之理”的基础上,凭借自身的能量,来为委托人解除法律难题的。律师是法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说客。它需要准备的绝对不只是法律言辞本身,靠一张铁嘴是不行的。
同法官、检察官、警察一样,它首先得学习法律。那种认为当律师只要会走后门的说法,是对中国司法生活的天大误解。把法律学得非常精通,是做律师的入门功。周杏梅肯定是懂得这一点的。当律师之后,由于法律知识准备不足,她把办案之余的全部时间都用于学习,以致她有一天看见自己竞有了一个20来岁的儿子,觉得晃然若梦。她没有更多地照顾儿子的衣食住行和学习,因为她还在学习和成长,她甚至忘记了分娩之痛。作为一个母亲,没有一些经验让她理解孩子长大这一事件,无疑是最痛苦的事,但孩子恰恰在这个过程中理解了她。儿子从来不给她找麻烦,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成人那种自立的能力。为了报答孩子,她希望孩子跟着她做律师,以免除一些人生上的拼搏之苦,但儿子考上律师之后还是选择了商业。她无法从儿子身上找出她培育的痕迹。还有一件事她终生难忘:1984年全省律师统考,她高烧到40度还走上考场,主考官说,像周杏梅这样的人应当让她破格过关,但她还是考出了好成绩,既然高烧到40度能走向考场,就一定能考出好成绩。然后她读了大学,读了研究生,还上了中国最高律师班。自信帮她战胜辛苦,但她的自信战胜不了自己的儿子。
想做好一个律师,更重要的一点还是和司法界以及社会各界处理好关系。这并不是为了在诉讼中好走门子,而是在寻求一种法律沟通。法律本身是钢铁一般的条律,但它的背后和深层其实是人文生活的汪洋大海。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法律意识和它特别的法律习俗。比如你是一个律师,一切人品的知识的准备都很充足,但你缺少司法人气,你怎么帮人打官司?不管是法官还是检察官还是公安部门的人,包括与那个案子相关的其它行业的人,都瞧不上你,都不理你,你的水平怎么发挥?甚至连当事人都怀疑你,你又该怎么办?你可能连案子都不会有。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所以,你必须很快让这个圈子的人知道你、理解你、信任你。
周杏梅刚当律师时,她遭遇的事情便是没人理她,更沮丧的是,办案中常常有人把她推出门外。她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呀。但好处是,她是那种天生有信念的人,她认为这是暂时的,只要自己努力,不断能办出一些让人们信服的案子,司法界以及社会就会接纳她这个人。于是,她不管案子大小,只要觉得有道理就接下来办,她要用全部的知识、品格和精力把那个案子办好。果不然,她出道不久那个与一棵大白菜相关的案子给她赢得了美誉。而办案之余她做的事情是,拜访人,请教人,与人谈话,约人吃饭,想着法子与人多打交道。这些人当然都是将来可能和她在工作中发生关系的人。这些事当然都是很功利的。而在这些疲备而杂乱的社交生活中,她的心情当然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周杏梅天生快乐,她言谈举止对人们的感染力,总算把她和的司法界粘合起来,从而使她度过了做律师的社会基础这一关。
想做一个很好的律师,还得有健康的身体。不说别的,就说每天成十个、几十个人的谈话,谁能坚持下去?再说东奔西跑地调查取证,有时候还得与恶劣的大自然环境抗争,谁又能忍耐了那份辛苦?本来身体很好的周杏梅当了律师后,身体确实有过撑不下去的时候,但她还是坚持了下来。而现在,不管再忙,她从来精力旺盛,就像共产党员那样,已经有了一副铁打的骨头。
再比如随时随地注意训练自己的口才和思辩能力,以及对生活细节的观察、判断、记忆和描述的能力一一回过头想,我们会发现,不仅是周杏梅,包括很多著名律师,他们打胜的精典案件很多都来源于对那个案子精辟的分析和解说,并在一些细节上击败法庭上的诉讼对手。就像周杏梅所说,好律师都是驾驭司法细节的高手,他们的胜利往往出现在诉讼内容的细部,换句话说,诉讼的胜败,从法律业务上讲,其实是技术问题,技术指你作为一个律师的业务水平。说到这里我想起一句话,有人说周杏梅是律师界的“江湖高手”,周杏梅承认社会上有这个称呼,但从她的表情和言辞上,判断不出她对这个称呼的态度,她只是说,作为一个好律师,既要有良好的知识和理论素养,同时要看你是否对律师业务已经熟透了,甚至熟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就是你分析案情的深度、反应的速度和判断问题的准确度,以及你实现自己司法目的的社会技巧;律师工作说到底是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在这一点上,咱们案子上见,谁也别吹牛;一个闪光的法律思想只能取悦于听众的耳朵,却帮不了老百姓任何忙,要这样的思想干什么?只能是让人们更加失望,对法律失去信心;而我,在这些方面充满信心。
周杏梅更重要的业余生活还是做女人。采访之前,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女人是那种富于诗意的性别,她的价值取决于她身体语言能表达多少内心的美丽和人类动人的情感,以及生活中最细腻的感觉,而这一切都是感觉形态的,但一个女人却做了律师,就像做了军人一样,她每天生活在冰冷的理性和血性中,这是否会剥夺女性天然的那种品质?见到周杏梅之初,我曾觉得我一定料事如神,但一次晚餐改变了我的看法:那次吃的是海鲜,在座的人中有一位作家,一个女法官,一个检察官坯有一个很像样的老板。那一次周杏梅像一个女孩,也许是喝了一点酒,她的脸红朴朴的,笑得非常开心,她说,“我可爱打扮啦,穿最新款的衣服.戴最好的首饰,每天都不重样的,但是,”她拍拍那个女法官的肩膀说,“工作的时候我从来穿的都是西装,你们看,”她的手柔软地从上身滑下,说,“这些天总是开庭,这身皮已经穿了一周没离身了。”她穿的是一身黑色西服。她像孩子一样对大家说,“我特别想让大家都说我很漂亮。”我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别人对她是否很喜欢,也是她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周杏梅显然不是为了这个而打扮自己的,不过,她明白,一个人越出名,就更应当注意个人形象。
周杏梅从里到外已经完全职业化了。就像一个企业文化大师所说:如果一个人连职业气质都没有,或不明显,这至少说明他(她)至今还没有认真地工作过。(但他们却在痛快地生活着。)
周杏梅有什么样的业余生活?其实没有,因为她把生活的一切都作为诉讼的准备,就像她所说,诉讼场上,其实是一场诉讼参与者人生整体资源的战争,不管案子大小,胜利都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