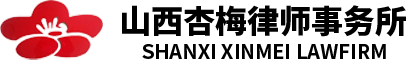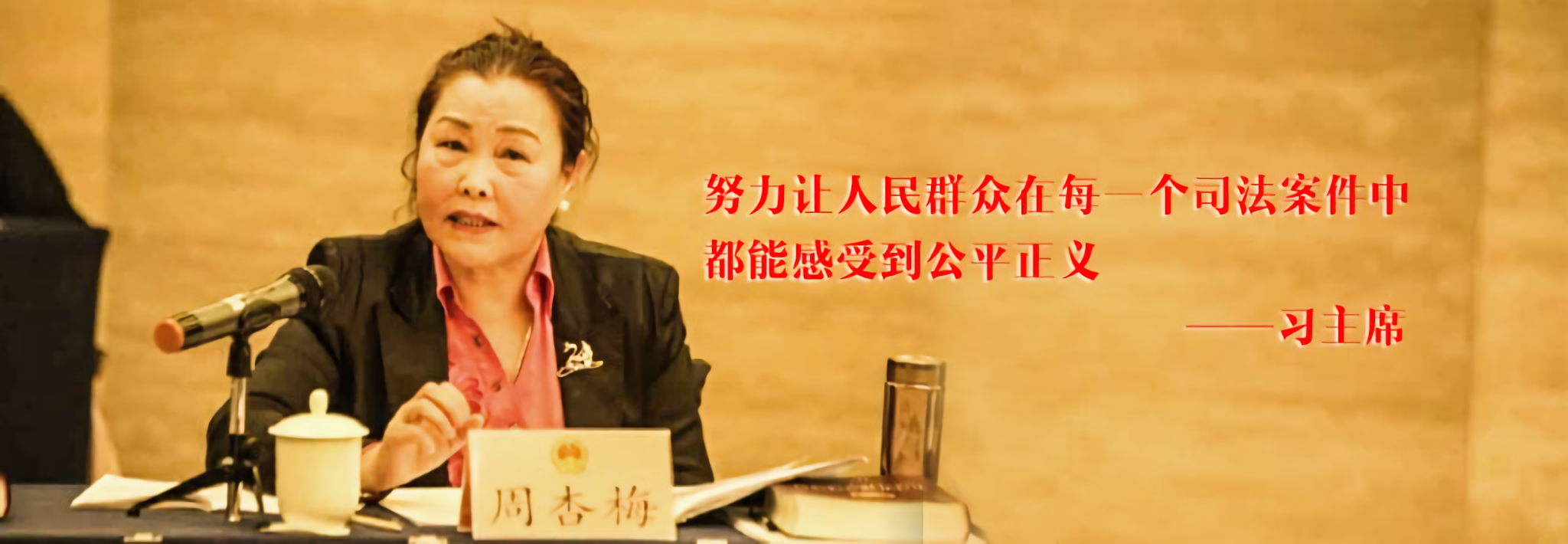她生于50年代,从走入社会到现在,一直在风风火火地追求理想。她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中最缺乏的那种把理想当作生命之火燃烧的人。她代表着新时代做人的希望。
20多年前从县城打进省城,几年后,她终于选择了和自己的性格非常适应的工作一一律师,这奠定了她成功的基础。她的故事有力地证明了,人们如何处理性格和工作的关系,对事业的成功意义非凡。
她在律师界出道不久就是律师事务所主任,但1999年她——于不惑之年,一个任何人到这些时都要开始担心生存的年龄段——辞去了公职,办了个人律师事务所。这个极富于挑战性的辞职对社会述说着很多问题。
由于办案在山西出了名,1994年她作为山西律师唯一代表,荣幸地参加了中国首次律师访美代表团,受到美国司法界好评,美国大律师瓦罗在美国以她的名字建立了一个法律性质的网站,叫“杏梅网站”。
她是山西第一个被国家批准以个人名字作为律师事务所名字的人。
她的“杏梅律师事务所”选择了太原最上品质的小区佳地花园作为办公地点,这在山西律师界是第一家。
她正面临的挑战是,诉讼律师向非诉讼律师的转型。前一种律师的主要是帮人打官司,后一种律师主要职责则是用法律服务的手段协助整合社会秩序,这是中国整个法制改革面临的新课题,周杏梅首先觉醒,她是否能再次成功?
请阅读周杏梅的故事。
近20年前,我写过一个律师,那是个为民请命的律师。20后我写周杏梅,她是什么人物?
在几个公众场所我见过她,并且握过手,说过“你好”之类的话,在我的印象中,她个头不高,心气很高,她风风火火的作派,使我觉得她内心还留有青春。热爱修饰自己,言谈举止却随心所欲。朋友介绍说,她不像40多岁的女人,我的感觉是,她根本没意识到“老”这个字。老什么,才40多岁,正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亲贤北街佳地花园的写字楼里,有她的律师事务所。走在楼道里,我感受到大理石的色韵和它清凉的气息。律师事务所外问人影杂乱,听谈话都是些与案子有关的人。被她的助手领进里间,我又见到周杏梅。她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我们隔桌相视而笑,使我觉得我与她的距离非常遥远。是她洪亮的声音和飞快的语速把距离一点一点削减下来。她是在接电话中与我谈话的。让我惊讶的是,她每接完一个电话,竟然还能接住俩人刚才的话头。
她的笑容使她显得很有魅力。
她说,她是山西晋南霍县(现改为霍州)人,父母生了她们5个,她是老大,从小家境一般。老大比母,也许是这个原因,养成了她一个男人般的性格。她说她从小争强好胜,上学时,别人的字写得比她好,考试成绩比她好,她就不服气,她把睡觉和玩耍的时间全用在学习上,直到超过别人为止。她还能说、能闹、能打,女孩之躯,“不让须眉”。不过,她并不是那种捣乱的孩子,她只是个性强,人要厉害,班干部也得当,小组长,班长,少先队队长,她都当过,而且是换着当。她说她的少年是在自信中度过的,她从来没想过有什么做不成的事情。
1973年,她高中毕业,1974年,她被安排到霍县县委组织部工作,1975年,她当了霍县三教公社团委书记,一年一个台阶,她只21岁。作为一个在县城长大的女孩,应该说她“混”得很好,但几年后,她离开了老家霍县,到了省城。她承认进城是她性格的必然,也符合那代人的梦想。梦想是什么?“其实就是往最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走,不断地离开,不断地走,但个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却一点都不知道。”这时她已经有了一份美满的婚姻,但类似周杏梅这种人,是不会被一般人意义上的那种幸福所困住的,因为真正的幸福只在她的内心,她终生会会矢志不移地寻找下去,直到再没有一点力气。
找她的电话又打进来了,一会儿手机,一会儿桌上的电话,基本上都是谈案子的。在周杏梅与对方通话时,我发现她回答问题非常仔细,唯恐对方听错一个字似的,但她的语气很霸气,“就这样办吧”,等等,这也许已经是周杏梅和这个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于是我感到,这个城市的很多人,认为已经离不开周杏梅,我想这才是周杏梅进军太原后,给自己确立的真正价值。
当然,周杏梅离不开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使她感受到一个更强大的周杏梅存在,至少,在这个城市的佳地花园的那个办公室的那个巨大的写字后坐着,她的感觉会更好一点。
一个人的办公室就是一个人的事业基地,这个没错。
周杏梅,周大侠,周律师
用中国文化分析中国律师,会发现很多中国律师身上都有着侠客文化的品质,这和西方是不同的。西方的律师工作是用法律的方式实现个人功利,而中国律师在出道之初,内心就流淌着正义之血。比如周杏梅,尽管周大侠这个说法并没有大律师周杏律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得广泛,但我相信她从小就是那种抱打不平的人,她同情弱者,嫉恶如仇。尽管这是中国文化中很偏狭的一部分内容,但它造就了很多孤胆英雄:一种总是企图用个人品质和能量征服世界的人。
从1984年到如今,周杏梅做律师已经18年,在这个过程中,她抽时间修完了法律学六类大学和研究生的全部课程,完整地读完了法律学学士和硕士,但谁也没有想到1984年她考律师的情景是这样的:那是文革后我们这个城市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考律师,当时,被律师这个辞深深打动的年轻姑娘周杏梅来到招考场所,激动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然后按照要求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文中表达了自己正义的天性,和对国家法律的责任。周杏梅考上了。好多年后回想起此事,周杏梅在感到纳闷的同时,她猜想到,那次能顺利地考上律师,除了自己口头和文字两种语言的表达能力强,肯定还沾了自己个性的光。因为她个性中那种正义感和勇气,正是“为民请命”这个“律师阶段”所需要的一种基本精神。所以我说,周杏梅最早考上律师,并不是她法律造诣的成功,而是当时中国一种律师意识对她这个人的接纳——我认为这是周杏梅做一个中国式律师最雄厚的根基。还有一件事是值得回忆的:1984年在太原市南城区律师事务所做律师不久——当时正值最初的严打——周杏梅遇到这样一个案子:一个可怜的卖西瓜的年轻人,被别人欺负得实在难以忍受,在被对方用扁担抽打的间隙,抓起西瓜摊上的西瓜刀捅向对方。当时以及后来并没有死亡现象发生,但卖西瓜的年轻人却要为那一刀付出性命。周杏梅接到这个案子,面前首先出现的是那些社会恶棍狰狞的面孔。当时她的法律知识还不足以解释社会上复杂的法律纠纷,但她就是感到这个年轻人不应当死,并且感到受到惩罚的应当是另外一种人。
她带着对这个年轻人的同情和对社会恶棍的愤怒,给年轻人写了一份申诉状,那个年轻人无罪释放了,周杏梅哭了。她哭的是正义果真有那样的力量,哭的是自己终于做了一件梦想中的事,一件快意的事。她说她的哭仅仅来源于激动。而她获得的是那年轻人的母亲给她送来的一棵特大的白菜。她说,她不能回想那棵水灵灵的大白菜。
周梅做律师的第二年就做了太原市第四律师事务所的主任,18年来,她什么案子都办过,办得都很漂亮,像张某某抢劫案、“小洞天酒家”行政案、太海贸易公司经济赔偿案、迎泽区糖酒公司副食批发部房产案、中国银行山西分行侵权案、中国银行运城支行担保纠纷案、山西省人民医院侵权案、现役军人胡某某俩兄弟强奸杀人案、山西某县商业局局长巨额资金来源不明案、洪洞县“山西金融第一案”等等,都是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案子,并被法学家和司法同仁认为是可供研究的精典案件,同时她用法律服务的手法还促成了很多经济合作,但是,她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个办刑事案件的高手。
1995年周杏梅在北京审判“四人帮”的那个法庭上做的那场辩护,是她作为律师获得全国名声最重要的一次契机。这就是上边提到的现役军人胡某某俩兄弟强奸杀人案。案情是这样的:胡某某,山西人,在北京当兵,起诉人说他在探亲回乡的一天晚上,与弟弟到另一个村轮奸了一个女子,奸后杀人,而帮助他们完成犯罪行程的工具是他们自己家的汽车,当时是冬天。接到为胡某某俩兄弟辩护的委托后,作为女性,周杏梅当然为现役军人干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感到愤慨,但经过调查取证后她发现,根据那女子死亡的时间和被成功者分析报告证实的俩兄弟可能做案的时间,中间只有半小时,而两个村之间有5里路,并且那是个冬天,发动汽车也得消磨不少时光。汽车从这个村开到那个村。两个人翻墙到了那家院里。找到那个女子的房间实施轮奸再把她杀掉。周杏梅计算了一下,在那种环境和条件下,半小时俩兄弟绝对不可能干那么多事。周杏梅感到这个案子是有问题的,至于说问题是什么——即使永远弄不清,但那兄弟俩绝不应当成为刀下之鬼。周杏梅在法庭上为俩兄弟据理力争,她的杀手锏就是对俩兄弟犯罪时间的分析。周杏梅的逻辑使那个法庭晃然大悟。俩兄弟一个保住了命,一个只判了6年。说到这里,周杏梅说,关于法律的正义,其实就是为弱者出气,为受冤枉的人保命,这不仅是律师的责任,而且是法律的德性。
她办的还有许多案子是值得记忆的:比如上述某县商业局局长被控有巨额资金来源不明,其实这个局长很正统很老实很廉洁,但对方不仅把他告到法庭,而且因为他无法提供一个人三年前在某地见他时所穿的衣服(包括内衣),而将他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作为他的辩护人,周杏梅意识到对方的胡搅蛮缠。因为她与对方有过接触,当场就向对方提出:那天你看见我穿的什么衣服?对方语塞。她接着问:你记得我穿的什么内衣?对方还是语塞,听众大笑。她接着问:局长与那个人接触已经过了三年多,咱们那次见面到现在才半个月,你为什么就忘记了我穿的衣服?
周杏梅在法庭上占了上风。周杏梅说,那天听审的人很多,人山人海,她说大家听的并不是那个局长是否犯罪,而是法律的道理。确实,法律上有很多道理是很打动人心的,尤其是它公平地解释现实生活的时候。
一对年近八旬的老年夫妇在太原一个最基层的法庭闹离婚,谁也想不到周杏梅会为这样小的一个案子到法庭为老太太做代理,到那样小的一个法庭上去辩护,但周杏梅去了一一只要周杏梅参与的案子,这案子一定很重要,而且很有趣——听众挤满了那个楼道,围住了那个小楼。其实那个离婚案很简单,周杏梅只所以接过这个案子,只不过出于对一对老年人的同情,和对一份老年婚姻的尊敬。这个案子能辩出什么精彩来?但听众听得全神贯注,时而报以热烈的掌声。采访过一个当时的听众,那人说,我们其实是听周律师对老百姓那份感情,而且只要是周律师办的案子,肯定差不了。我不能说这是名人效应,但也不排除这种因素。不过,律师能做到这个份上,那绝对是她用法律的手段在社会上“积了大德”。
就像很多人说,周杏梅已经是山西响当当的大律师,如果她只接那些标的很大的经济大案,现在不知道已经发到什么程度,但是,她还是对那些充满正义、同情和怜悯内涵的案子更感兴趣,并且常常会接一些最底层的老百性的冤屈案,而有些案子她是分文不取的,甚至要贴钱。原因只有一个:她容易被正义所打动,常常是自己打动自己。